【长评】世纪的伪证——评《狂野时代》
更新时间:2025-11-25 04:02:35

作者 / 两只青蛙跳下锅
排版 / 两只青蛙跳下锅
封面 / 喵刀
Où en êtes-vous?(你身在何处)
——蓬皮杜中心
吊诡的是,《狂野时代》看起来很符合Nicole Brenez在“jeune, dure, et pure”的导论中对实验电影总结。但事实上,如同迈克尔·哈内克的伪情感、朱利亚·迪库诺的伪身体主义、奉俊昊的伪场面调度,毕赣近几年的作品也完全是对实验电影的伪证。但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点,即在戛纳电影节上大放异彩。
首先提出观点与态度是有必要的,《狂野时代》它首先不再和一部电影如何成为有关,而是一种与影迷、与电影史相对抗的世界电影之缺陷。

(1)设备
对于实验电影的设备,Nicole将其总结为“总有不同的方式来布置、设定或操作事物,并且往往更加富有人文精神和令人兴奋”,但《狂野时代》似乎只是粗略地概括了关键词中的一部分,“令人兴奋”。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兴奋?它对于任何一名观众来说都只是在自作感动地呈现自己“致敬”电影时的样子。它会令谁兴奋?所有人,通过无知与诈骗。它会令所有人感受到怎样的兴奋?同样的兴奋,只要是在电影院的兴奋。但毕赣在戛纳首映观看这部电影的兴奋感难道会和在观众在平遥首映观看的兴奋感相同吗?如同结尾处用一座电影院表达所有观众情绪的影像从来没有真实过,无论是在《阿尔卡萨戏院的座椅》还是在《红色死神》里,没有一位观众的兴奋是一致的(甚至有冲突!),《狂野时代》从一开始就在字母中抛出了最狡猾、最虚伪的几个字:那是电影!
至于被忽略的其他几个关键词,所展现出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过程。在周滔关于《山之南》、《山之北》的放映构想中,他把屏幕安置在观众的两侧,让观众仿佛被山峦包围。这样的设备的不同方式总是与空间、密度、速度等基本元素息息相关,最基本的方面是它必须通过对操作的扩展来突破常规的物质与非物质的强度。而在《狂野时代》当中,那唯一被突破的是所有的运动性。但可笑的是这样的突破带来的是身体的僵化、空间的平面、时间的停止,仿佛它扩展的是电影中所有的癌细胞,最终变得萎缩/静止。波宗对斯科雷基的批判,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批判致敬电影史的毕赣:必须确信系统地去强调作品的“过度”之处,即那种猥亵的小孔,好不容易让那些忘恩负义且失落的能指、同性恋牛仔和好莱坞美人开口说话,从而把电影史重写为一种“后电影”的无礼视角。那种把侏儒展现成只有狡猾身体的视角是哪种有礼的视角?就像我们在预告片中所看见的那样,每个镜头都集中了一个动作、一个造型、一个强有力的预感,但是将它们组合起来时,然后呢?
正如戈达尔总是为不同图像之间的关系取名,在毕赣近日的电影里只能看见对这种图像的无端串联,被扩展的只是数量而非方式。我所看见的设备,无非是被一个人所超控的世界级超大型团队想要只用一台摄影机来耗尽电影史的全部能量,他们总是以为能在数个明星(另一种设备)的姿态里充满这种能量,维利里奥所形容的战争影像在这里如同一场自爆。如果还有人问,就算有这么多伪证,但对电影的致敬难道不富有人文精神吗?自从《狂野时代》无端地“水浇死园丁”开始,便已经不再是致敬而是疯狂的臆想了。

(2)心理机器
所谓电影,那是一种超越之物。时间:它超越了此时此刻的时间,如同一双掌管胶卷的手,左手往前拉长,发掘更多梦想之物;右手托住胶卷,仿佛在回放之前的记忆,从过去缝隙中重新创造。左手:它意味着超越现实,当我们所看之物无法再创造出更多的梦想之物时,左手指向的便是那些现实之外的空间,是一种从格里菲斯到吕克·穆莱之间的跨越。右手:它意味着超越记忆,那些我们所回望的终将是对它无限次的重读,直到最后变得完全不同,过去之时间被无限地往前推进,直到雅克·特纳与让-克劳德·比耶特的关系如同《物质剧院》的戏剧和现实。总之那是把一切可能转译为不可能,即使没有终点也要把那不可能重新转换回可能。
《狂野时代》究竟哪一点抵达了这种超越之心理?对于粉丝,或许ta们只是想看看毕赣又拍了什么新作亦或是易烊千玺在大银幕上的脸庞;对于影迷,或许他们早已被毕赣的风格与致敬电影史的名声所吸引。作为明星,《狂野时代》又究竟超越了易烊千玺的哪一点?难道是说镜头在他耍酷姿势面前停留时间更长了吗?还是他突破了明星中吸烟的纪录:从民国抽到九十年代末。作为作者,难道把卢米埃尔、表现主义、默片、有声片、时空顺序揉在一起就能变成超越了吗?那我岂不是把牛筋、牛腩、牛腱、牛杂、牛头摆在一起说我买了一头牛?
这是一种几乎提不起梦想的兴趣的电影,在苦妖出现的时候,寺庙之外的世界被磨平,它给了我们什么观看的权利去幻想这外面的世界?在易烊千玺表演魔术的时候,它又给了我们什么观看的权利去欣赏这过程中动作与身体的美丽。一切一闪而过转瞬即逝,以姿势之名忽略了调度的可能性,又以致敬之名忽略了其他的电影形式,但事实上《狂野时代》又真的有什么独特形式吗?如果又有人要问,这只是毕赣的怀念与致敬之作他并不想超越什么,那作为作者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呢?即使它只是为了怀念,《狂野时代》也几乎不具备任何时代的风格,它所做的只不过是把电影史本应有的精彩凝结在平庸的此刻。它的超越,只不过是把我们所有的期望超越为了失望与无奈。

(3)以视觉探索世界
“那种革命性的时间体验、传统的抽象与具象之关系的持续颠倒——理应促使我们将这些重要影像从实验室中带出”,
Nicole Brenez如此形容探索之美,并补充这种探索将会如同探险家的笔记一般为后世提供素材。而哪位实验电影人不是在各类影像运动中寻找素材并颠覆这种观察?
而《狂野时代》并没有颠覆任何一类观察,对卢米埃尔的?那是一种嘲讽,只因为《水浇园丁》永远失去了原初那可爱的气质;对表现主义的?它甚至连观察都算不上,舒淇绕过各种黑影与古怪的建筑,这一长镜头是很美丽是很迷人,可惜它是个哑巴和衰弱的身体;对类型片的?如果谍战片只用展现几个逼供的动作、如果奇幻片只用抽半个小时烟、如果超英片只用使用一下超能力,那实验室与外面的世界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我一直在好奇这些动作的重量,是哪种让一开始的观众散开,又是哪种让死人做了一个梦,又是哪种让散开的观众重新回到电影院让破败的影院重新建立。但他们只是露出了一种表情,好似很疑惑,却一无所知地完成了这个动作。一个没有理由存在的动作,这又是哪种时间体验?
那种探索家永远都能用他所有发现做依据的辩论姿态不存在于在此时此刻毕赣的身上,不仅因为他懒得发现,也因为他懒得辩论。这将不能为后世任何一类电影提供素材(但除了那些同样作为世界电影之缺陷的电影),这种发现并不具备知识,它的生产也并不具备任何震慑。正如达内所举的那个经典例子,《阿诺德·勋伯格电影配乐导论》的最后一部分之所以会让我们恐惧,并不是因为那些导弹在影像中被生产、在影像中被投放,而是因为我们深刻知道这些导弹曾在二战中杀死了无数人曾被投放在广岛长崎。即使把要求放到最低,把各种摄影机的、灯光的、声音的、表演的生产抛开,就算只留下对“致敬电影”这唯一电影对象的体验,但在这种无观察之观察中,致敬的无生产之生产又能带来哪种体验。毕赣无非是小学坐在最后一排开小差的学生。

(4)实验疆域
一个电影的世界的疆域是它所有运动元素不断流变的趋向。即使是最小的,《我的城市》中阿克曼身体与房间物品的接触将会产生炸弹般的威力,而在《我你他她》中身体、物品与空间之间的碰撞又会产生性质上的改变:当阿克曼挪动床铺后,观众将会在一个全新的角度看房间、房间将在全新的角度看物品、物品与阿克曼之间的感知关系也发生变化。相互成倍增长、向外成倍扩大,作为实验的过程。
但究竟能在《狂野时代》中看见哪种流变,至少它不是影像运动的流变,在苦妖变成狗走出庙门之后,这座寺庙并没得到任何新的视角,声音、天气与光照、地面的颗粒如同天蒙蒙亮时那样。那条狗从眼前一闪而过,但却只是一个错觉。流变只存在于石头-妖怪-狗这三个身份之间,除了电影,文字可以记载这样的关系、绘画可以呈现这样的变化,甚至人与人之间可以口头传述,那还要电影干什么?它对影像运动抽象与具象之间的关系毫无意义。明明有两个镜头有720种剪辑方式(如果我们使用沃尔特·默奇的计算方式),而《狂野时代》总是选择最平庸的那一种,明明在正反打之间可以产生720种状态,可是在张志坚和小孩的正反打中,除了小孩莫名其妙学会超能力并感动了张志坚,无事发生。
这似乎是在说,我们在用一颗全景长镜头持续跟踪阿克曼挪动床位。我们讨厌这种感知,实验电影讨厌这种伪装的动态。Nicole Brenez追求的是将电影的构造点作为探究的对象,是设备、叙述、叙事、色彩、形式之间的流变,是要在这流变里改变认知和感知,如同她在结论型或考据型的文章中总是大量列举作者与电影的名字,却不多加解释,这是一种叙述与叙事之间的美。而对《狂野时代》来说,流变存在于超级资本主义与电影史之间,是在凝视身体的时候被无差别地入侵与洗脑。正是通过明星的经济活力,它强迫我们相信这是用力的、流动的,但这是假装的活力。如果说它如同实验电影一样排斥着什么,那恐怕是排斥着我们的身体与欲望。

(5)图像历史与批评
实验电影将整个电影铭记在心:它曾是什么,以及它本可以是什么。毫无疑问,毕赣似乎觉得自己很在意这一点,也完全重视这一点。只用一点小手段强调动作与身体就觉得自己把观众在看电影时的感官全部强调出来,再混搭一点风格就觉得是在做电影史的梦。可电影史是个白日梦,它不是那种像《狂野时代》里的那样把活人改造成放映机就能做梦的梦,观众需要调整好状态,工作人员需要准备就位,世界还在运转。他以为这样做就能在连接起百年前的图像,而图像是判断力与批评的抉择,而不是在一个毫无层次的幻想中做梦。
当我看见舒淇在剧院里按动老式照相机时本应有一段历史发生,即使在梅里爱的电影里他也会让火箭插进月亮的眼睛来补充空白,可毕赣却深深地陷入幻梦的假象当中。在烟馆里一只巨大的手在调动着场景,可它却永远不能像格里菲斯那样在空间的变化时产生情感,只剩下一扇扇无辜的、可怜的门,一群被硬纸壳包裹着的被压得找不回历史定位的人。在“大他者”被缓缓推进虚无的洞里时,它似乎想让我们等待着什么,等着等着,电影院恢复了,人们进去看电影了。再次回到最原始的问题,是什么的欲望让他们走进这座从破败到修复好的“博物馆”,没有人知道,他们就这样走进这座电影院,而影厅里有的人就这么被打动。在这永不存在激情的致敬里,电影尚未知晓它自己的历史,那些观众也未知晓他们自己的历史。“永远不会存在的电影《狂野时代》的预告片”,总之一吹即散。

我以与《狂野时代》同样恶劣的面貌来书写文字,它像一张狗皮膏药贴在电影史上,那就也让它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实验电影上,并从一种根本不属于它的角度来击碎它的神话。它似乎的确拥有实验电影的重要特质,极端的场景道具设备运用,极端的主题,极端的感染力,极端的呈现形式(五感),同样也想迫切地想制造出能够被写进资料库的图像。而实验电影的感知力从来都是用“除此之外”来表现,毕赣却成为“大家都这么说”的典范。一个是前进口号,一个是营销口号。即使都是以那种纯粹的意志来拓展电影的言语,可是一个向上一个向下。不存在任何悖论,这就是恶劣本身。与电影之间的感觉可以像《旅途中的日子》那样在仅仅一个剪辑后将我们脱离出来却迟迟怀疑电影里的那块银幕和我们眼前银幕的分离,可以像《神圣车行》那样踏进一家实在的影厅里却迷失了任何的时空感,可以像《红色死神》那样在电影院里把自己变成数个图像——这些都是基本的品质,用最平庸的话来讲也应该是简易的情感。而决不能像德勒兹所描述的那样在摄影机与人物的面对面中失去感知——这也是从一开始就失去了的东西,用直接的几个字幕卡和我们面对面讲清楚:这是电影、这是梦,从此之后不忍直视。
有谁不会满怀期待地去想象,因为毕赣钟爱极端的技术形式,那电影通过技术会变成什么样?就好像电影在德尼·拉旺的身体里会变得怎么样。后者在悄无声息种从一个世界通过传送门到达另一个世界(的确,轿车内的声音仿佛被封闭在房间里的回声),没有人知道哪个世界是虚拟的哪种演绎,哪个世界又是现实的哪种回归。虚拟与现实,记忆与证据,影院和街道,观众总是会出神,电影总是会往别处瞥一眼。而毕赣,却可以做到用技术死死地盯着一个人并强迫他每一分钟都要发生变化。在没易烊千玺的空间里必须出现他的手,在妖怪变身的时候必须让他看见,在小孩使用超能力的时候必须让他在旁边陪着,而易烊千玺也必须要随着这些情景表演出吸血鬼的样子、抽大烟的样子、死人的样子、痛苦的样子、虔诚的样子......可谁又愿意在他冗杂的身体里待这么久,这让人害怕电影,集中营的人同样也害怕劳作。


或许毕赣从一开始的成功就是来自于运气,如果说是退步,那又怎会有如此惊人的转变。那在《路边野餐》中的是一种超过人体极限的超自然力量,角色为何发出那种孤僻的方言,虽然说是他们习惯了,但其中仍隐藏着一种他们自己仍不可知的力量,和悠久的地方历史有关。而那些建筑呢?仿佛站立在其中的人永远与其格格不入,无论从哪个时期(即使是工业革命之前)来看都会觉得那是个贫穷的地方。虽说那些人却早已习惯,可是谁又能真正习惯居住在瀑布边上、成天吹着坏掉的风扇?在摄影机坐上过山车环视周围时、在快门角过小画面而变得迟钝时,我总觉得自己亏欠这一切。但他们却能够习惯这里,恐怕也有一种我尚未认识到的力量吧,或许我该从野人和酒鬼的位置上、从墙壁上的火车、火车外的时钟上注视这一切吧。
而在《地球最后的夜晚》里又有着无论如何都感受不到的力量,你要让我相信萦绕在汤唯身上的神秘感?恐怕回忆他的黄觉自己都不相信,那些回忆总是在一瞬间回到现在,在啃完苹果的一瞬间在枪响的一瞬间,甚至连一点回味的资格都没有。这甚至令我怀疑那个回忆者的动机是否不纯,是否这只是一件突然插入进来的若无其事的事,只是走在大街上突然在口袋里抓出从家里带出来的糖。这一切太扁平了,扁平到甚至怀疑影像本身,这究竟是回忆的运动,还是在长镜头上把各种奇观捆绑起来的叙述空间?它没有重量,却让人一步就跨进了充盈的虚无中。那是一种只曾在《裹尸布》中体验过的感觉,在承受了无数个无比光滑、平均的优质镜头后,却在与盲人的交媾中终于感受到充沛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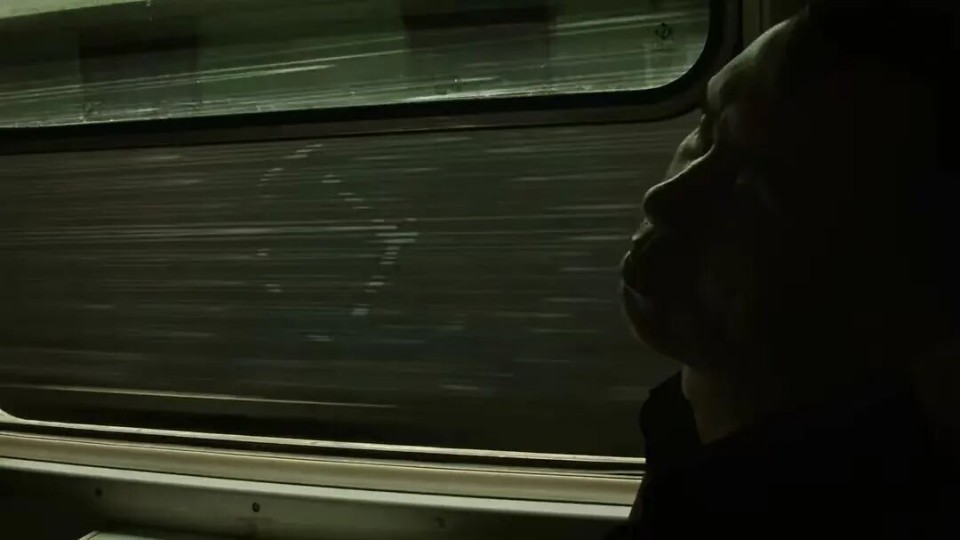

但《地球》效果怎么会同等有效,即使同样也是光滑的优质镜头,毕赣却连喘息的机会都没给我们,不停留的回忆真的重要吗。那《路边野餐》呢?早就说过他们怎么可能真的习惯这种生活,语言和身体早就想要逃离。一旦画面变得同样光滑后陈永忠再次在屋顶操着方言问道“卫卫在哪里”时,背后却是明亮的楼房和反射阳光的摩托车后视镜,这怎么让人相信眼睛和耳朵接收的事同一种信息。就如同在《狂野时代》中,有尊严的人不会就这么轻易相信电影史长那样。所以毕赣从来没转变过,他只不是因为以前没那么多资金,误打误撞表现出了一些才华,一旦资金充足就没有任何影像之间的关联值得相信。毕赣的电影是投机者的电影。
甚至那些所谓极端形式却从未极端地表达过,在《地球》的长镜头里,黄觉乘坐的滑索在一个安全的位置停了下来。即使那个团队要用巨大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来完成这个长镜头,但他依然让除了这资本运作之外的任何事物变得安全,甚至不敢更凶狠地把枪对准养蜂人,他为了保持回忆的情感而遗忘了在这过程中煎熬的身体。为了告诉我们电影有多丰富,不惜在易烊千玺脸上塞进一万张面孔,但无论从哪种变化都不能感知到这些面孔与世界形成的角度,变化太快以至于变得扭曲(这正是易烊千玺作为演员与毕赣的契合之处)。他如今只用令人惊讶的灵感来展现出实验人的姿态,可布拉哈格临终前的《中国系列》却在遥远的地理与文化距离上呈现出神秘学式的兴奋。毕赣不过是依靠金钱伪证自己具有实验性,怪物在啃食你的脑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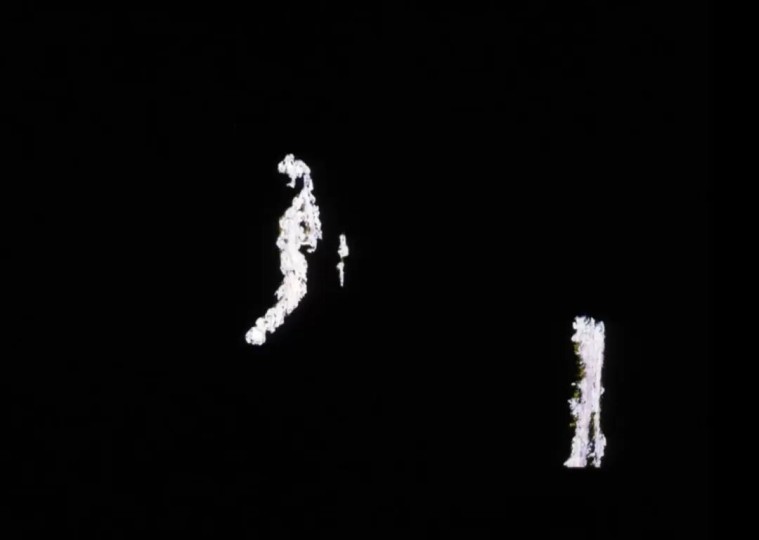
f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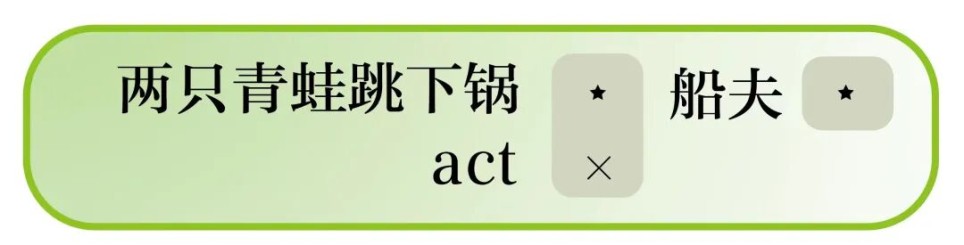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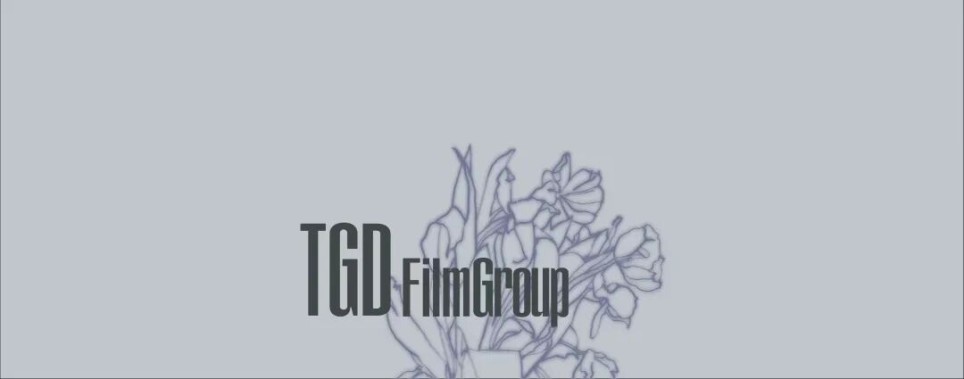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上一篇:谁tm把毕赣送去读mfa了?
 性 · 梦 · 死亡——主观解读《狂野时代》
性 · 梦 · 死亡——主观解读《狂野时代》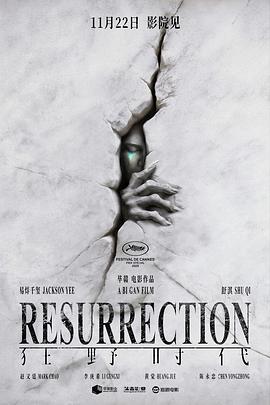 《狂野时代》是把艺术还给艺术
《狂野时代》是把艺术还给艺术